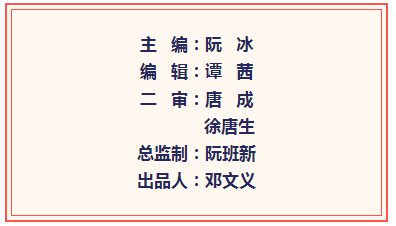清明雨谒
作者:陈华国
清明时节的雨,总在黎明前悄然停歇。山雾自谷底升起,将整片废墟笼罩在氤氲水汽中。鼓胀的帆布包静静躺在山路入口,里面整齐叠放着纸钱,一坛陈年佳酿在包底沉甸甸地坠着,新买的香烛散发出淡淡的檀香味。红泥沾满鞋底,每一步都在山路上留下清晰的印记,像一串通往过去的密码。
山路上的茅草没过脚踝,在晨风中荡起绿浪。几只鹧鸪被惊起,扑棱着翅膀消失在雾霭深处。远处布谷鸟的啼鸣忽远忽近,与记忆中生产队的晨钟渐渐重合。那口挂在槐树下的铁钟,曾经在每一个清晨准时响起,唤醒沉睡的山峦。钟声里,一个披着蓑衣的身影扛着锄头走向田埂,背影渐渐融入晨雾。转过一道山梁,熟悉的废墟赫然眼前。坍塌的土墙爬满青藤,敞开的薯窖像一张张饥饿的大嘴,吞噬着往日的记忆。半块青瓦静静躺在草丛中,冰凉沁骨。是堂前的滴水瓦还是祠堂飞檐的勾头?记忆忽然模糊起来。瓦片上细密的纹路像掌心的皱纹,记录着风雨的痕迹。
通往祖茔的小径早已被蕨类占领。锋利的草叶划过,渗出细小的血珠。苦楝树枝散发清苦香气,混合着泥土的腥味,故乡的气息弥漫开来。转过山梁,被砍的古树桩上,嫩绿的新芽奇迹般冒出。最粗壮的柏树桩周围,野蔷薇攀缘而上,绽放粉白花朵,如为逝去的生命戴上花环。水井已被泥石流淹没,厚厚的青苔下,井沿上的青石被岁月磨得圆润发亮。恍惚间,木桶撞击井壁的闷响在耳边回荡。井台边的栗子树,随着搬迁被伐作柴薪,却在三丈外的土坑里长出新苗,歪斜的枝干执拗地伸向水井方向,像是要找回失落的记忆。
祖坟前,三炷香点燃,青烟笔直上升,在静止空气中画出神秘的符号。一杯陈酿洒下,醇香顿时在晨雾中弥漫开来。话音未落,山风乍起,纸灰打着旋儿飞向天空,如诉无声的回应。半堵残墙边,梨树花开如雪,花瓣飘落在熟悉的汽水瓶上。瓶身的"橘子"二字已经模糊,但阳光下泛着微光。恍惚间,甜中带涩的滋味在空气中弥漫,欢笑声从记忆深处传来。
晒谷场上发黑的水泥板泛着惨白的光,裂缝里钻出的野草已齐膝高。1977年搬迁时来不及收拾的箩筐与草帽早已腐朽,唯独汽水瓶静静倒卧,成为时光的见证。裂缝里一丛蒲公英探出头来,金黄色的花朵在风中轻轻摇曳。正午时分,山雾渐散。一只蓝纹蝴蝶停落在墓碑上,翅上的花纹宛如靛蓝布衫的纹路。洗得发白的衣服,袖口磨出了毛边,却永远整洁得体。此刻,蝴蝶的翅膀在阳光下微微颤动,投下细碎的阴影。收拾祭品时,泥土里突然现出半个"红星"搪瓷缸。斑驳的蓝边在阳光下若隐若现,正是当年共用的茶缸。缸中积着雨水,浮着几片榆钱。夏夜纳凉时的薄荷茶香,寒冬清晨的热粥蒸汽,都在记忆中苏醒。搪瓷上的红星已经褪色,但那个火红的年代仿佛就在昨天。
返程路上,布谷鸟开始此起彼伏地啼叫。车窗外,牛栏、猪圈、菜园在新绿中渐渐模糊。石碾静卧荒草间,当年写满标语的土墙爬满紫藤,开出淡紫色的花串。清明时节的雨,年复一年落下,滋润着故乡记忆。斑驳的搪瓷缸被轻轻摩挲,追寻的从不是逝去的年代,而是清明雨中永恒的温情。插秧时的蛙鸣、收割时的月光、挑担时的晨霜,都沉淀为心底最珍贵的琥珀。最后一个山弯隐入雨雾,眼帘轻合。地图上的圆点,记忆中的灯火,都化作清明雨滴,渗入泥土孕育新芽。故乡的故事终将在年复一年的春雨里延续,如同栗子树根上重生的新苗,生生不息。
雨又下了起来,打在车窗上形成蜿蜒的水痕。后视镜里,故乡的轮廓渐渐融化在雨雾中。废墟间倔强生长的新绿,记忆中永不褪色的画面,已经深深烙在心底。方向盘上的手微微收紧,知道明年清明,雨停时分,还会回来。土地上的生命,从未真正离开;清明时节的雨,永远滋润着记忆的根系,让怀念在时光中枝繁叶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