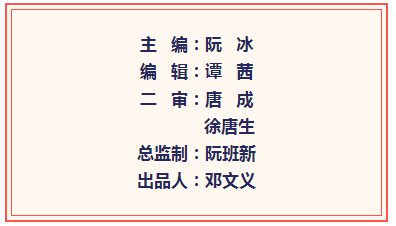母亲再也回不去的村庄
作者:张凯
母亲总爱摩挲那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边角卷起毛边,像被岁月啃噬的牙齿,画面里穿碎花布衫的姑娘站在歪脖子老槐树下,两条粗黑的麻花辫垂在胸前,眉眼间漾着山涧清泉般的笑意 —— 那是她二十岁离开村庄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。
四月的槐花又开了,簌簌飘落。母亲戴着老花镜,安坐在沙发里,指着一遍遍抚过照片里斑驳的白墙,忽然喃喃道:“这老槐树,怕是早被雷劈断了吧。”我望着她鬓角新添的白发,忽然惊觉,那个藏在照片里的村庄,已与母亲相隔五十多个春秋的迢迢长路,仿若山高水长,难以丈量。
我曾陪伴母亲重返她的村庄,记忆里,那里始终萦绕着一股潮湿的泥巴味。母亲老家在北方,“吱呀”一声推开那扇大铁门,迎面便是一堵青砖照壁,与南方人家敞亮通透的小院截然不同。泥巴小巷弯弯曲曲,晨光总在巷口徘徊许久,才舍得爬上灰扑扑的瓦檐。逢年过节,巷道里飘着炸麻花、油条的焦香,邻家阿婆的梆子声“笃笃”敲着,混着驴车、马车碾过石板路的轱辘声,搅成一团暖融融的烟火气。
老屋堂屋的长条木桌还在吗?桌角有道月牙形的豁口,是她十岁那年摔碎瓷碗,慌乱中用铁勺磕出来的。如今想来,那道疤痕倒像时光烙下的印记,见证着无数个灶台前的晨昏。母亲常念叨,北方的灶台连着土炕,烧火时柴火噼啪作响,整间屋子都暖烘烘的,不像南方的煤炉,总带着股呛人的烟味。
母亲的亲戚众多。表哥家的羊圈挨着三叔的磨坊,二舅妈的菜园子斜对着村口的老井。母亲说起这些时,眼里会亮起久违的光,仿佛又看见小孩子们举着柳枝在麦场追逐,惊起一群群灰扑扑的麻雀。可自她二十岁南下通山嫁给父亲,这方水土便成了回不去的旧梦。在外婆离世那年,她连夜坐了二十小时的绿皮火车,踩着积雪回村奔丧。那时老槐树还在,枝桠间挂着几串褪色的红布条,是村里人祈福系上的,带着朴素的心愿。
“年纪大了,村里怕是回不去了。”母亲摩挲着照片,突然说了句。我想起她平日里总爱窝在沙发里看电视,嘴角挂着淡淡的笑,仿佛世间万物都与她无关。可每当电视里闪过那一望无垠的平原画面,她的眼神便会变得悠远,像是穿越千山万水,回到了那个炊烟袅袅的村庄。
母亲素来节俭,剩菜剩饭都舍不得丢弃。可每逢老家亲戚来电话,她又会偷偷塞给我钱,让我寄点回去,是一份她的心意。她看着电视,絮叨着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,谁家盖了新房娶了媳妇。那些散落在记忆里的人和事,在她的讲述中渐渐鲜活起来,如同老墙上的青苔,在时光的雨水中重新舒展。
前几年冬天,老家的表哥打来电话,说老宅子拆了。母亲握着听筒的手微微发抖,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声音。挂了电话,她在楼下路边的石凳上,坐了整整一下午,望着远处的山峦发呆。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,横亘在现实与记忆之间。
“其实早就该拆了。”母亲突然转身,眼角泛着水光,“那些老房子,漏风漏雨的,早该翻新了。”可我分明看见,她转身时偷偷抹了把脸。等我走进她的房间,她正捧着个红绸包,里面是几张泛黄的信纸,还有一枚银戒指。
“这是你外婆留给我的。”母亲把它套在指节上,“这也算是我当年的嫁妆啦。”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,在她脸上镀了层银霜,恍若岁月的薄纱。我忽然想起龙应台在《目送》里写的: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”而母亲与村庄的缘分,又何尝不是如此?
如今,那座村庄的模样早已消失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,化作一片平整的土地。母亲依然会在某个清晨,对着照片发呆。她不再念叨着要回去看看,只是偶尔会说:“人老了,记性就差了,有些事再不记着,就真的没了。”
窗外的槐花又落了一地,洁白如雪,恰似记忆里村庄的雪。我忽然懂得,有些地方,并非回不去,而是即便回去了,也寻不见记忆中的模样。就像母亲与那个村庄,早已在时光的长河里,沉淀为彼此最珍贵、最温暖的回忆。